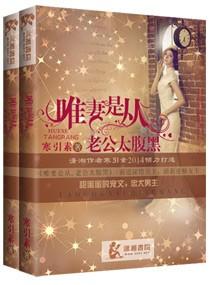匪我思存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洋葱小说网www.3ponet.com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“守守。”阮江西仿佛下了什么决心,终于告诉她,“易长宁回来了。”
守守的脸色比江西预想的要平静很多,过了好一会儿,她才反问了一句:“是吗?”
“我昨天在学校遇见他,他回来参加一个研讨会。”阮江西有点唏嘘,“三年了,他好像一点都没变。”
三年--这样漫长,又这样短暂:漫长得仿佛已然天荒地老,所有的前尘往事,不过是漫漫烟尘,扑上来,呛得人没头没脑,呼吸艰难;短暂得却仿佛只是昨天,一切清晰得历历在目,几乎令人无法面对。
三年前她多懒啊,胸无大志。而江西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,什么都要做到最好,事实也确实如此。不管是专业课,还是基础课,甚至连学校最有哄台传统、嘘声四起的“广院之春”晚会上,江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雷鸣般的掌声。而她成天混大课、抄作业,阮江西偶尔怒其不争:“守守你将来怎么办?”
守守笑嘻嘻地说:“一毕业就结婚,然后让易长宁养我呗。”
阮江西被气得咒她:“要是易长宁不要你了呢?”
“他怎么会不要我呢?”
那样自信满满,却从未想过,会一语成谶。
和易长宁分手的时候她风度全无,狼狈不堪,以至于后来守守一想起来,就会自嘲,这辈子也算是泼妇过一回。只是揪着易长宁的衣襟,放声大哭,不管他说什么就是不放手。
最后给江西打电话,江西赶来的时候,她还独自坐在那里泣不成声。那样的地方,虽然服务生都目不斜视,但她知道自己丢脸,可是易长宁那般绝情地不顾而去,她还有什么需要顾忌?
江西二话没说,拖起她就走,把她塞进车子里,一边开车一边恨铁不成钢似的说:“守守,为了一个男人你就这样啊?他不要你了你就这样啊?”
而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只会哭,把江西车上的一盒纸巾都哭光了。江西载她回自己的公寓,扔给她一套睡衣,然后说:“要哭好好哭,出了浴室,你要再哼一声,我立马把你扔回家去。”
那天她在浴室里哭了很久,也许是一个小时,也许是四个小时,因为最后浴缸里的水全冷了。她冻得感冒了,一直没有好,先是发烧,挂了几次点滴,不发烧了,只是咳嗽,断断续续咳嗽了两三个月,又查不出什么大毛病。这一场病,虽然不是什么大病,可是整个人就瘦下去了。
遇见纪南方是在会所大堂,一堆人众星捧月,而他个子高,即使在人堆里也非常抢眼。守守看到他,正犹豫要不要打招呼,他也看见她了,突然停步,“咦”了一声,就说:“守守,你怎么瘦成这样?”
一帮人早就哄然大笑,有人说:“南方,瞧你把人家小妹妹折磨的。”
也有人认识她,笑着说:“你们别瞎扯了,这是南方的妹妹。”
另外有人就叫:“南方你还有妹妹啊?是不是叫北方?”
纪南方笑骂那人:“滚!”回头向那帮人介绍,“这是叶慎守,我妹妹。”
那帮狐朋狗友都是见多识广的,立刻就有人想起来:“慎字辈啊,是叶家人?”更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恭维:“哟,昨天我们还跟慎宽一块儿打牌呢,没想到他妹妹这么漂亮。”
叶慎宽是她的大堂兄,叶家长房长子,自然交游甚广。一帮人立马集体认下了这妹妹,二话不说拉她一起去骑马。
其实他们人人都带着女伴,纪南方也不例外,是一个艳光四射的女子,漂亮到令守守总觉得眼熟,想来想去,终于想起来好像是选秀出身的某新星,只记不起来她叫什么名字。那女子倒是很落落大方:“叶小姐可以叫我可茹。”
这下提醒了守守,终于想起她的名字叫张可茹,于是客客气气称呼她:“张小姐。”
只没想过这位张小姐从来没有骑过马,被扶上马背后大呼小叫,只差要哭了,害得骑师教练一头冷汗:“张小姐……张小姐……请您放松一下,你这样紧紧抓着缰绳,马会比你更紧张的。”
守守并没觉得好笑,她第一次骑马的时候还很小,根本不知道怕。二伯带她和几个堂兄去军马场,真正的大草原,纵情驰骋,那种无拘无束,只有天高云淡,四野旷阔。呼呼的风声从耳旁掠过,直想叫人放声高歌。事实上她也真的唱歌了,跟几个堂兄一块儿,从《打靶归来》一直唱到《潇洒走一回》,最后连嗓子都吼哑了,可是很快乐,非常的快乐。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没有办法形容,也很轻易地渲染了一切。连一向不苟言笑的二伯,也跟他们一块儿唱起“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,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
纪南方养着一匹十分漂亮的温血马,从马厩牵出来的时候守守只觉得眼前一亮,高大神骏,真正的德国汉诺威。其实纪南方和叶慎宽一样,吃喝玩乐,无一不精,无一不会。就这匹血统恨不得可以算到祖上十八代的名种,就看得守守赞叹不己:“前不久我在电视台实习,做一档体育节目,郑重其事地访问了几个马术俱乐部,都没见着这么好的马。”
纪南方只是嘲讽:“一个丫头,做什么体育节目?”
守守不服气:“有本事你叫奥运会不准女选手参加啊?性别歧视!”
永远是这样,她跟纪南方待一块儿超过半个钟头,就会开始吵架。
小时候他还肯让着她一点,因为她小,又是女孩子,所以他根本不屑跟她吵。等他从国外回来,她也在念大学了,过年的时候他陪他父亲来给她爷爷拜年,长辈们在楼上说话,他跟她几个堂兄在楼下闲聊,偶尔聊到舒马赫,她插了句话,两个人于是卯上了。她口齿伶俐,而他反应迅捷,两人从法拉利车队一直激辩到巴赫《Chaconne》的三十二个对称变奏,犹未分出胜负来。最后还是她另一个堂兄叶慎容忍不住,“哧”的一声笑出来:“瞧瞧他们两个,像不像斗鸡?”
叶慎宽哈哈大笑,纪南方不由得也笑起来,但心有不甘。这次辩论不了了之,但第二次重逢,两人不知道为什么事,又开了头,一发不可收拾。从此叶慎宽只要看到她跟纪南方碰一块儿,就会掏出烟盒:“你们先吵着,我去抽支烟。”
她一时气结。其实叶慎宽跟纪南方还有他们那群人都永远拿她当小孩子,她刚开始跟易长宁谈恋爱,叶慎宽知道的时候非常意外:“丫头,你还小呢。”
她有点气鼓鼓:“我马上就十九了,还小什么啊?你十九岁的时候,女朋友都换过好几个了。”
这句话差点没把叶慎宽给噎死,后来叶慎宽对纪南方不胜唏嘘:“哎,连守守都开始交男朋友了,我们真是老了。”
“扯淡!”纪南方对当时怀抱美人、杯端醇酒的叶大公子嗤之以鼻,“你不过就比我大两岁,这么早就想着金盆洗手浪子回头?那还不如现在就回家陪媳妇去。”
“你别说,”新婚不久的叶慎宽不无得意,“结婚还是有好处的。为什么?玩起来方便啊,只要你媳妇不说话,老爷子一准睁只眼闭只眼,反正连自己老婆都不吱声,老头还能说啥?所以南方啊,结婚吧,一了百了,这就是结婚的好处。”
纪南方身边也有女人,她于是半嗔半恼,说:“哎哟,说出这样的话来,真是坏透了。”
纪南方倒毫无顾虑,捏住她的下巴哈哈大笑:“我们这帮人啊,个个都坏透了,你呀,是落入虎口了。”两个人一时笑一时闹,腻成一团。
这天骑马,倒出了小小的意外,张可茹最终还是从马背上摔下来,把脚给扭了。不知有没有伤到骨头,但当时张可茹摔在沙场里,半晌站不起来。
众人都没有在意,连纪南方都只是给司机打了个电话,叫他送张可茹去医院,唯独守守说:“我陪她去医院吧。”
这下连张可茹都十分意外,连声说:“叶小姐,不用了,我自己去就行,你好好玩,别扫兴。”
“我陪你去。”守守执意。
纪南方也没太放在心上:“那你陪她去吧。”随口嘱咐司机,“照顾好叶小姐。”
守守啼笑皆非,明明张可茹才是受伤的那一个。上车之后张可茹有点歉意:“真的没必要,这样麻烦你。”
守守倒觉得心中有愧,其实她本意不过是想找个借口开溜而已。就因为这点愧疚感,她很认真地陪张可茹挂号,扶她进电梯,拍完片子后司机帮忙去取,她陪张可茹一块儿坐在长椅上等,结果有护士路过,立刻认出张可茹来,很尽责地发出粉丝的尖叫,然后一堆人围上来,七嘴八舌地要签名。
张可茹没什么架子,笑吟吟地帮他们签名,守守被隔在一堆人外头,她甚少有这样被冷落、被排除在外的时候,不由得觉得有点好笑。其实这张可茹很年轻,比她大不了多少,眉目如画,精致的一张脸,小小的,上镜一定好看。
回去的车上张可茹却皱起眉头来:“这下好了,十天半月开不了工,回头公司一定骂死我。”
她很怕她的经纪人,据说是行内最有名的脸酸心硬,捧红无数大牌,所以一呼百应,张可茹怕他怕到要死。张可茹非拉着守守跟她去吃饭:“要死也先做个饱死鬼,等我吃饱了再给他打电话,省得他骂得我吃不下饭。”
这样精致漂亮的一个人,发起嗲来更是楚楚动人,守守禁不住她软语央求,陪她一块儿去吃饭。
张可茹是湖南人,吃辣,守守也嗜辣如命,两人对了口味,吃掉一桌子菜。张可茹吸着气,唇色殷红欲滴,嘴角微微一翘,说不出的妩媚好看:“真痛快,平常不让我吃,说怕坏嗓子。”
守守一时好奇:“连吃都不让随便吃?”
“是啊,也不让吃多了,天天就是沙拉啊水果啊,我上次忍不住吃了一对鸡翅,结果形体教练让我在跑步机上慢跑了整整三小时,哎呀惨死了。”
二十出头的女孩子,到底还有点孩子气,扮了个鬼脸:“反正我这次是罪无可恕,索性犯法到底。”
这么一说,守守觉得张可茹其实也蛮有趣的。
她很少跟哥哥们的女伴交往,其实也是家教使然,因为哥哥们的女伴永远只是女伴,从来不会有身份上的改变。
记得几年前叶慎宽曾交过一个女朋友,当时非常的认真,跟家里闹翻,搬出去住。最后的结局仍旧逃不了是分手,那是她第一次看到风度翩翩的大堂兄失态,他其实并没有喝醉,端着茶杯,站在花房兰花架子前,将一杯滚烫的毛尖,随手就泼在那株开得正好的“千手观音”上头。
而他的笑容微带倦意:“彩云易散琉璃脆。守守,这世上美好的东西,从来没办法长久。”
当时她大约只有十五六岁,皱着眉头有点愤愤:“大哥你太轻易放弃了,真爱是无敌的。”
现在想想,真是幼稚得可笑。
她跟张可茹也并没有深交,隔了两个月,偶尔遇到纪南方又带着张可茹一块儿吃饭,张可茹见着她,忙从手袋里取出几张票,笑着说:“上次的事还没谢谢你,这是我的演唱会,就在下星期,捧个场吧。”
守守当然接过去了,她同学朋友多,转手就送了人。
所以张可茹的经纪人赵石给她打电话的时候,守守觉得非常意外。
她的手机号并没有多少人知道,赵石打到她实习的栏目组,然后辗转问到号码。赵石虽然是圈中名人,不过这种过程一定很复杂、很艰难。而他的措辞很客气,也很小心。接到电话之后,她静静地听他讲完,沉默了几秒钟,才说:“那么,我去医院看看她。”
其实她真不该蹚这种浑水,但有那么一刻她心软了,因为自己也曾动过这样的傻念头,在易长宁不顾一切而去的那一刹那。
张可茹住在私家医院,她的经纪公司很小心,并没有让传媒发现这件事。守守带了一束花去,张可茹瘦了很多,一张脸更显得只有巴掌大,没有化妆,脸色显得很苍白,看到守守的那一刹那,眼底里只有一片茫然,倒显得有种少女般的稚气。
守守把花插起来,张可茹终于怯怯地问:“他还好吗?”
守守整理着花枝,新鲜的红玫瑰,绽放得那样艳丽,那样甜美,可是,明天就会凋谢了。如同大堂兄所说,彩云易散琉璃脆,这世上美好的东西,从来没办法长久。
张可茹见她不说话,有点慌张,问:“他是不是生气了?”
守守在椅子上坐下来,凝视着张可茹漂亮的大眼睛,然后叹了口气。
张可茹像只受惊的小兔子,不知道她要说什么。
守守不过把纪南方这么多年的女朋友们描述了一遍,有些是她亲眼见到的,有些是她听说的,有的美得惊人,有的也不怎么美,最长的断断续续跟了纪南方差不多两年,最短的不过两三天。分手的时候也有人哭闹,但纪南方处理得挺漂亮,他出手大方,从来不在钱上头吝啬。
最后张可茹说:“谢谢你,我明白了。”她的脸色已经平静下来,如同刚刚睡醒的样子,眼里渐渐浮起悲哀:“我知道我这样不应该,可我没有办法。”
守守想起小时候读过的词:
春日游,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年少?足风流。妾拟将身嫁与,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,不能羞。
是真的很爱很爱,才会有这种勇气,把一颗真心捧上,任由人践踏。
回家后她给纪南方打了个电话,他那端人声嘈杂,说笑声、洗牌声……热闹非凡,一听就是在牌桌上。守守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生气:“纪南方!我有要紧事找你。”
“啊?”他从来没听过她这种口气,一时倒觉得意外。电话里都听得见那边有人嚷:“南方,四筒你要不要?”
“不要不要。”他似乎起身,离开牌桌走向安静点的地方,嘈杂的声音渐渐消失了,他还是觉得莫明其妙,“到底什么事?”
“反正是要紧事,”她绷着声音也绷着脸,尽管知道他看不见,可是仍旧气鼓鼓的,“你现在马上出来见我,现在!”
她知道自己有点无理取闹,可是一想到张可茹,她总会想到自己。
这样没有出息,这样没有尊严,可是没有办法,只哀哀地等着那个人转过头来,但偏偏他永远也不再回头了。
纪南方接完电话走回牌室:“我有事,得走了。”
“别介啊,我这手气刚转呢。”陈卓尔第一个叫起来,“什么人啊,这么大能耐,打个电话来就能把你叫走?”
雷宇峥说:“谁也别拦着他,一准是办公室打来的,咱爸找他呗,你们瞧瞧他那脸色,《红楼梦》里怎么说来着,‘避猫鼠儿一样’。”
叶慎宽笑得直拍桌子:“雷二!雷二!咱们认得这么多年,我怎么不知道你还读《红楼梦》,这典故用的,哥哥我服了啊。”
“滚!”纪南方也笑起来,“我一妹妹找我,急事。”
“哟,什么妹妹呀?”叶慎宽揶揄他,“就这么让你放在心坎上,心急火燎的。”
纪南方正没好气:“你妹妹找我。”
“守守?”叶慎宽十分意外,“她找你干吗?”
“我怎么知道?电话里发脾气呢。”
“我这妹妹,打小被惯的。”叶慎宽不以为然,“小毛丫头能有什么事?一准又是没事找事。”
话虽这样说,到底纪南方还是去了,约在一间咖啡馆,服务生认得纪南方:“叶小姐在那边。”
灯光很暗,东南亚风格的矮几上点着蜡烛,浅浅的陶碟里漂着花瓣,守守正等得无聊,于是用手去捞那花瓣。她的手指纤长,很白,其实叶家人都生得这样白净。纪南方老嘲笑守守的几个堂兄都是小白脸,但她是女孩子,细白柔腻的皮肤,看起来像个瓷娃娃,此时拈起一瓣嫣红,嘟起嘴来,朝花瓣嘘地吹了口气。那雪白的手指被花瓣衬着,仿佛正在消融,有种几乎不能触及的美丽。纪南方想起古人说“指若柔荑”,忽然觉得这形容太不靠谱,茅草那样粗糙的东西,怎么会像手指?因为这样纤细柔嫩,仿佛碰一下就会化掉。
而烛光正好倒映在她眼里,一点点飘摇的火光,仿佛幽暗的宝石,熠然一闪。她的眸子迅速地黯淡下去,仿佛埋在灰里的余烬,适才的明亮不过是隔世璀璨。在这一刹那他有点想笑,这小丫头什么时候有了心事,而且还这样郁郁寡欢的。
抬起头来看到他,还是有点孩子似的气鼓鼓:“我等老半天了。”
“大小姐,我从城东赶过来。”他漫不经心地打发服务生,“矿泉水。”
然后摸出烟盒,还没有打开,她已经轻敲了一记桌子:“公众场合,我最讨厌二手烟。”
“你哥不也抽吗?”
她理直气壮:“你又不是我哥。”
“你喝咖啡?”他瞥了她面前的骨瓷杯碟一眼,“小孩子别喝这个,省得晚上睡不着。”
“你才是小孩子呢,”她倒不生气了,“再说我又没做亏心事,怎么会睡不着?”